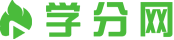在日常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,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。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?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,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,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一
在北平呆过的人总该懂得“人话”这个词儿。小商人和洋车夫等等彼此动了气,往往破口问这么句话:
你懂人话不懂?——要不就说:
你会说人话不会?
这是一句很重的话,意思并不是问对面的人懂不懂人话,会不会说人话,意思是骂他不懂人话,不会说人话。不懂人话,不会说人话,干脆就是畜、生!这叫拐着弯儿骂人,又叫骂人不带脏字儿。不带脏字儿是不带脏字儿,可到底是“骂街”,所以高尚人士不用这个词儿。他们生气的时候也会说“不通人性”,“不像人”,“不是人”,还有“不像话”,“不成话”等等,可就是不肯用“人话”这个词儿。“不像话”,“不成话”,是没道理的意思;“不通人性”,“不像人”,“不是人”还不就是畜、生?比起“不懂人话”,“不说人话”来,还少拐了一个弯儿呢。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后才说那些话,当着面大概他们是不说的。这就听着火气小,口气轻似的,听惯了这就觉得“不通人性”,“不像人”,“不是人”那几句来得斯文点儿,不像“人话”那么野。其实,按字面儿说,“人话”倒是个含蓄的词儿。
北平人讲究规矩,他们说规矩,就是客气。我们走进一家大点儿的铺子,总有个伙计出来招待,哈哈腰说,“您来啦!”出来的时候,又是个伙计送客,哈哈腰说,“您走啦,不坐会儿啦?”这就是规矩。洋车夫看同伙的问好儿,总说,“您老爷子好?老太太好?”“您少爷在那儿上学?”从不说“你爸爸”,“你妈妈”,“你儿子”,可也不会说“令尊”,“令堂”,“令郎”那些个,这也是规矩。有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假仁假义,假声假气,不天真,不自然。他们说北平人有官气,说这些就是凭据。不过天真不容易表现,有时也不便表现。只有在最亲近的`人面前,天真才有流露的机会,再说天真有时就是任性,也不一定是可爱的。所以得讲规矩。规矩是调节天真的,也就是“礼”,四维之首的“礼”。礼须要调节,得有点儿做作是真的,可不能说是假。调节和做作是为了求中和,求平衡,求自然——这儿是所谓“习惯成自然”。规矩也罢,礼也罢,无非教给人做人的道理。我们现在到过许多大城市,回想北平,似乎讲究规矩并不坏,至少我们少碰了许多硬钉子。讲究规矩是客气,也是人气,北平()人爱说的那套话都是他们所谓“人话”。
别处人不用“人话”这个词儿,只说讲理不讲理,雅俗通用。讲理是讲理性,讲道理。所谓“理性”(这是老名词,重读“理”字,翻译的名词“理性”,重读“性”字)自然是人的理性,所谓道理也就是的道理。现在人爱说“合理”,那个“理”的意思比“讲理”的“理”宽得多。“讲理”当然“合理”,这是常识,似乎用不着检出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大帽子,说“人是理性的动物”。可是这句话还是用得着,“讲理”是“理性的动物”的话,可不就是“人话”?不过不讲理的人还是不讲理的人,并不明白的包含着“不懂人话”,“不会说人话”所包含着的意思。讲理不一定和平,上海的“讲茶”就常教人触目惊心的。可是看字面儿,“你讲理不讲理?”的确比“你懂人话不懂?”“你会说人话不会?”和平点儿。“不讲理”比“不懂人话”,“不会说人话”多拐了个弯儿,就不至于影响人格了。所谓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,就是所说的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而“人话”要的也就是恕道。按说“理”这个词儿其实有点儿灰色,赶不上“人话”那个词儿鲜明,现在也许有人觉得还用得着这么个鲜明的词儿。不过向来的小商人洋车夫等等把它用得太鲜明了,鲜明得露了骨,反而糟蹋了它,这真是怪可惜的。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二
伦敦乞丐在路旁画画的多,写字的却少。只在特拉伐加方场附近见过一个长须老者(外国长须的不多),在水门汀上端坐着,面前几行潦草的'粉字。说自己是大学出身,现在一寒至此,大学又有何用,这几句牢骚话似乎颇打动了一些来来往往的人,加上老者那炯炯的双眼,不露半星儿可怜相,也教人有点肃然。他右首放着一只小提箱,打开了,预备人往里扔钱。那地方本是四通八达的闹市,扔钱的果然不少。箱子内外都撒的铜子儿(便士);别的乞丐却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
画画的大半用各色粉笔,也有用颜料的。见到的有三种花样。或双钩tolive(求生)二字,每一个字母约一英尺见方,在双钩的轮廓里精细地作画。字母整齐匀净,通体一笔不苟。或双钩goodluck(好运)二字,也有只用luck(运气)一字的。——“求生”是自道;“好运”“运气”是为过客颂祷之辞。或画着四五方风景,每方大小也在一英尺左右。通常画者坐在画的一头,那一头将他那旧帽子翻过来放着,铜子儿就扔在里面。
这些画丐有些在艺术学校受过正式训练,有些平日爱画两笔,算是“玩艺儿”。到没了落儿,便只好在水门汀上动起手来了。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,这些人还来了一回展览会。那天的晚报(theeveningnews)上选印了几幅,有两幅是彩绣的。绣的人诨名“牛津街开特尔老大”,拳乱时做水手,来过中国,他还记得那时情形。这两幅画绣在帆布(画布)上,每幅下了八万针。他绣过英王爱德华像,据说颇为当今王后所赏识;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时候。现在却只在牛津街上浪荡着。
晚报上还记着一个人。他在杂戏馆(halls)干过三十五年,名字常大书在海报上。三年前还领了一个杂戏班子游行各处,他扮演主要的角色。英伦三岛的城市都到过;大陆上到过百来处,美国也到过十来处。也认识贾波林。可是时运不济,“老伦敦”却没一个子儿。他想起从前朋友们说过静物写生多么有意思,自己也曾学着玩儿;到了此时,说不得只好凭着这点“玩艺儿”在泰晤士河长堤上混混了。但是他怕认得他的人太多,老是背向着路中,用大帽檐遮了脸儿。他说在水门汀上作画颇不容易;最怕下雨,几分钟的雨也许毁了整天的工作。他说总想有朝一日再到戏台上去。
画丐外有乐丐。牛津街见过一个,开着话匣子,似乎是坐在三轮自行车上;记得颇有些堂哉皇也的神气。复活节星期五在冷街中却见过一群,似乎一人推着风琴,一人按着,一人高唱《颂圣歌》——那推琴的也和着。这群人样子却就狼狈了。据说话匣子等等都是赁来;他们大概总有得赚的。另一条冷街上见过一个男的带着两个女的,穿着得像刚从垃圾堆里出来似的。一个女的还抹着胭脂,简直是一块块红土!男的奏乐,女的乱七八糟的跳舞,在刚下完雨泥滑滑的马路上。这种女乞丐像很少。又见过一个拉小提琴的人,似乎很年轻,很文雅,向着步道上的过客站着。右手本来抱着个小猴儿;拉琴时先把它抱在左肩头蹲着。拉了没几弓子,猴儿尿了;他只若无其事,让衣服上淋淋漓漓的。
牛津街上还见过一个,那真狼狈不堪。他大概赁话匣子等等的力量都没有;只找了块板儿,三四尺长,五六寸宽,上面安上条弦子,用只玻璃水杯将弦子绷起来。把板儿放在街沿下,便蹲着,两只手穿梭般弹奏着。那是明灯初上的时候,步道上人川流不息;一双双脚从他身边匆匆的跨过去,看见他的似乎不多。街上汽车声脚步声谈话声混成一片,他那独弦的细声细气,怕也不容易让人听见。可是他还是埋着头弹他那一手。
几年前一个朋友还见过背诵迭更斯小说的。大家正在戏园门口排着班等买票;这个人在旁背起《块肉余生述》来,一边念,一边还做着。这该能够多找几个子儿,因为比那些话匣子等等该有趣些。
警察禁止空手空口的乞丐,乞丐便都得变做卖艺人。若是无艺可卖,手里也得拿点东西,如火柴皮鞋带之类。路角落里常有男人或女人拿着这类东西默默站着,脸上大都是黯淡的。其实卖艺,卖物,大半也是幌子;不过到底教人知道自尊些,不许不做事白讨钱。只有瞎子,可以白讨钱。他们站着或坐着;胸前有时挂一面纸牌子,写着“盲人”。又有一种人,在乞丐非乞丐之间。有一回找一家杂耍场不着,请教路角上一个老者。他殷勤领着走,一面说刚失业,没钱花,要我帮个忙儿。给了五个便士(约合中国三毛钱),算是酬劳,他还争呢。其实只有二三百步路罢了。跟着走,诉苦,白讨钱的,只遇着一次;那里街灯很暗,没有警察,路上人也少,我又是外国人,他所以厚了脸皮,放了胆子——他自然不是瞎子。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三
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,真令我神迷心醉了。
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,霏霏的毛雨默然洒在我脸上,引起润泽,轻松的感觉。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,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。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,经了那细雨,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;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。
细雨如牛毛,扬州称为毛雨。
大约也因那蒙蒙的雨,园里没了秾郁的香气。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;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。园外田亩和沼泽里,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,少壮的麦,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。这些虽非甜美,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,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。
看啊,那都是歌中所有的:我用耳,也用眼,鼻,舌,身,听着;也用心唱着。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。于是为歌所有。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,听着;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。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四
扬州从隋炀帝以来,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;称道的多了,称道得久了,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。直到现在,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,他会点头或摇头说:"好地方!好地方!"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,在他心里,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;他若念过《扬州画舫录》一类书,那更了不得了。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,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,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;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它。若是想呢,——你说他想什么?女人;不错,这似乎也有名,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?——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,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。
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,在我看,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。诚然,北方今年大雨,永定河,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,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;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儿水,但太平衍了,一览而尽,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。有水的仍然是南方。扬州的夏日,好处大半便在水上——有人称为"瘦西湖",这个名字真是太"瘦"了,假西湖之名以行,"雅得这样俗",老实说,我是不喜欢的。
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,曼衍开去,曲曲折折,直到平山堂,——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——有七八里河道,还有许多杈杈桠桠的支流。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,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,和别处不同。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,法海寺,五亭桥;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。金山你们是知道的,小金山却在水中央。在那里望水最好,看月自然也不错——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。"下河"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,人不免太多些。法海寺有一个塔,和北海的一样,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,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。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;但还有一桩,你们猜不着,是红烧猪头。夏天吃红烧猪头,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;可是在实际上,挥汗吃着,倒也不坏的。五亭桥如名字所示,是五个亭子的桥。桥是拱形,中一亭最高,两边四亭,参差相称;最宜远看,或看影子,也好。桥洞颇多,乘小船穿来穿去,另有风味。
平山堂在蜀冈上。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;"山色有无中"一句话,我看是恰到好处,并不算错。这里游人较少,闲坐在堂上,可以永日。沿路光景,也以闲寂胜。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。蜿蜒的城墙,在水里倒映着苍黝的影子,小船悠然地撑过去,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。船有三种:大船专供宴游之用,可以挟妓或打牌。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,在船里听着谋得利洋行的唱片。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?其次是"小划子",真像一瓣西瓜,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。乘的人多了,便可雇两只,前后用小凳子跨着:这也可算得"方舟"了。后来又有一种"洋划",比大船小,比"小划子"大,上支布篷,可以遮日遮雨。"洋划"渐渐地多,大船渐渐地少,然而"小划子"总是有人要的。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,也因为它的伶俐。一个人坐在船中,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,简直是一首唐诗,或一幅山水画。而有些好事的少年,愿意自己撑船,也非"小划子"不行。
"小划子"虽然便宜,却也有些分别。譬如说,你们也可想到的,女人撑船总要贵些;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啰。这些撑船的女子,便是有人说过的"瘦西湖上的船娘".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,但我不很知道。据说以乱头粗服,风趣天然为胜;中年而有风趣,也仍然算好。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,或尚不伤廉惠;以后居然有了价格,便觉意味索然了。北门外一带,叫做下街,"茶馆"最多,往往一面临河。船行过时,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。船上人若高兴时,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,或一两种"小笼点心",在河中喝着,吃着,谈着。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,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。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,他们不怕你白吃。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:我离开扬州,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,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;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。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,名字也颇有好的。如香影廊,绿杨村,红叶山庄,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。
绿杨村的幌子,挂在绿杨树上,随风飘展,使人想起"绿杨城郭是扬州"的名句。里面还有小池,丛竹,茅亭,景物最幽。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历落有致,迥非上海,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。"下河"总是下午。傍晚回来,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,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,一手微微摇着扇子;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。这时候可以念"又得浮生半日闲"那一句诗了。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五
我是一个国文教师,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可以说也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。这就决定了我的作风,若是我也可说是有作风的话。我的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。一方面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这地步,一方面也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这一路。我是个偏于理智的人,在大学里学的原是哲学。我的写作大部分是理智的活动,情感和想象的成分都不多。虽然幼年就爱好文学,也倾慕过《聊斋志异》和林译小说,但总不能深入文学里。开始写作的时候,自己知道对于小说没希望,尝试的很少。那时却爱写诗。不过自己的情感和想象都只是世俗的,一点儿也不能超群绝伦。我只是一个老实人,或一个乡下人,如有些人所说的。——外国文学的修养差,该也是一个原故。可是我做到一件事,就是不放松文字。我的情感和想象虽然贫弱,却总尽力教文字将它们尽量表达,不留遗憾。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,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,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,想多少可以补救一些自己的贫弱的地方。已故的刘大白先生曾对人说我的小诗太费力,实在是确切的评语。但这正是一个国文教师的本来面目。
后来丢开诗,只写些散文;散文对于自己似乎比较合宜些,所以写得也多些。所谓散文便是英语里的“常谈”,原是对“正论”而言;一般人又称为小品文,好似对大品文而言,但没有大品文这名称。散文虽然也叙事、写景、发议论,却以抒情为主。这和诗有相通的地方,又不需要小说的谨严的结构,写起来似乎自由些。但在我还是费力。有时费力太过,反使人不容易懂。如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里有一处说到“无可无不可”,有“无论是升的沉的”一句话。升的“无可无不可”指《论语》里孔子的话,所谓“时中”的态度。沉的指一般人口头禅的“无可无不可”,只是“随便”“马虎”的意思。有许多人不懂这“升的沉的”。也许那句话太简了,因而就太晦了。可是太简固然容易晦,繁了却也腻人。我有一篇《扬州的夏日》(在《你我》里),篇末说那些在城外吃茶的人回城去,有些穿上长衫,有些只将长衫搭在胳膊上。一个朋友说穿上长衫是常情,用不着特别叙出。他的话有道理。但这并不由于我的疏忽;这是我才力短,不会选择。我的写作有时不免牵于事实,不能自由运用事实,这是一例。
我的《背影》、《儿女》、《给亡妇》三篇,注意的人也许多些。《背影》和《给亡妇》都不曾怎样费力写出。《背影》里引了父亲来信中一句话。那封信曾使我流泪不止。亡妇一生受了多少委屈,想起来总觉得对不起她。写《给亡妇》那篇是在一个晚上,中间还停笔挥泪一回。情感的痕迹太深刻了,虽然在情感平静的时候写作,还有些不由自主似的。当时只靠平日训练过的一支笔发挥下去,几乎用不上力量来。但是《儿女》,还有早年的《笑的历史》,却是费了力琢磨成的。就是《给亡妇》,一方面也是一个有意的尝试。那时我不赞成所谓欧化的语调,想试着避免那种语调。我想尽量用口语,向着言文一致的方向走。《给亡妇》用了对称的口气,一半便是为此。有一位爱好所谓欧化语调的朋友看出了这一层,预言我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。我也渐渐觉得口语不够用。我们的生活在欧化(我愿意称为现代化),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,也在现代化,其实是自然的趋势。所以我又回到老调子。所谓老调子是受《点滴》等书和鲁迅先生的影响。当时写作的青年很少不受这种影响的。后来徐志摩先生,再后来梁宗岱先生、刘西渭先生等,直接受取外国文学的影响,算是异军突起,可是人很少。话说回来,上文说到的三篇文里,似乎只有《背影》是“情感的自然流露”,但也不尽然。《背影》里若是不会闹什么错儿,我想还是平日的训练的原故。我不大信任“自然流露”,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教师。
国文教师做久了,生活越来越狭窄,所谓“身边琐事”的散文,我慢慢儿也写不出了。恰好谢谢清华大学,让我休假上欧洲去了一年。回国后写成了《欧游杂记》和一些《伦敦杂记》。那时真是“身边琐事”的小品文已经腻了,而且有人攻击。我也觉得身边琐事确是没有多大意思,写作这些杂记时便专从客观方面着笔,尽力让自己站在文外。但是客观的描叙得有充分的、详确的知识作根据,才能有新的贡献。自己走马看花所见到的欧洲,加上游览指南里的一点儿记载,实在太贫乏了,所以写出来只是寒尘。不过客观的写作却渐渐成了我的唯一的出路。这时候散文进步了。何其芳先生的创作,卞之林先生的翻译,写那些精细的情感,开辟了新境界。我常和朋友说笑,我的散文早过了时了。既没有创新的力量,我只得老老实实向客观的描叙的路走去。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,很合脾胃,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。从前曾写过几篇论说的短文,朋友们似乎都不大许可。这大概是经验和知识还不够的原故。但是自己总不甘心,还想尝试一下。于是动手写《语文影》。第一篇登在《中央日报》昆明版的《平明》上,闹了点错儿,挨了一场骂。可是我还是写下去。更想写一些论世情的短文,叫做《世情书》。试了一篇,觉得力量还差得多,简直不能自圆其说似的,只得暂且搁下。我是想写些“正论”或“大品文”,但是小品文的玩世的幽默趣味害我“正”不住我的笔,也得再修养几年。十六年前曾写过一篇《正义》(见《我们的七月》),虽然幼稚,倒还像“正义”,可惜没有继续训练下去。现在大约只能先试些《语文影》。这和《世情书》都以客观的分析为主,而客观的分析语文意义,在国文教师的我该会合宜些。
我的写作的经验有两点也许可以奉献给青年的写作者。一是不放松文字,注意到每一词句,我觉得无论大小,都该从这里入手。控制文字是一种愉快,也是一种本领。据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很不讲究文字,却也成为大小说家。但是他若讲究文字,岂不更美?再说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样大才力,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?为一般写作者打算,还是不放松文字的好。现在写作的青年似乎不大在乎文字。无论他们的理由怎样好听,吃亏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,不是别人。二是不一定创作,五四以来,写作的青年似乎都将创作当做唯一的出路。不管才力如何,他们都写诗,写散文,写小说戏剧。这中间必有多数人白费了气力,闹得连普通的白话文也写不好。这也是时代如此,当时白话文只用来写论文,写文学作品,应用的范围比较窄。论文需要特殊的知识和经验,青年人办不了,自然便拥挤到创作的路上。这几年白话文应用的范围慢慢儿广起来了,报纸上可以见出。“写作”这个词代替了“创作”流行着,正显示这个趋势。写作的青年能够创作固然很好,不能创作,便该赶紧另找出路。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最大的出路,便是新闻的写作。新闻事业前途未可限量,一定需要很多的人手。现在已经有青年记者协会,足见写作的青年已找出这条路。从社会福利上看,新闻的写作价值决不在文艺的写作之下,只要是认真写作的话。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六
1、当他的背影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时,我进来坐了下来。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2、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,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,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。
3、要用闲暇去触摸风景,要用愉悦的品味去触摸眼睛
4、一群学者翩翩王子可以谈论秦晋时期的美好
5、我赶紧擦干眼泪,怕他看见,也怕别人看见。当我再往外看时,他已经抱着朱红走了回来。
6、当我在徐州见到父亲时,看到院子里乱糟糟的,一想到祖母,我的眼睛就湿润了。
7、那年冬天,我祖母去世,我父亲的工作也被取消了,真是祸不单行啊。
8、他用手把它举起来,又把脚收回来。他肥胖的身体微微向左倾斜,显示出努力的迹象。
9、灯光一亮,就变得很重了。那偶然闪烁的光芒,是梦中的眼睛。
10、我看见他头戴黑布帽,身穿黑布马褂,身穿深蓝色棉袍,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地弯下身子。
11、后来,我父亲写信说他可能很快就要走了。
12、要到达那个平台,就得穿过铁轨,跳下去,爬上去。我的父亲是个胖子,所以走到那里很费劲。
13、我的父亲是个胖子,所以走到那里很费劲。
14、哦,当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,我是多么聪明啊!
15、当他年轻的时候,他出去谋生,自己做了许多大事。那个晚年是如此的颓废!他很自然地被悲伤所压倒。
16、然后我看到了他的背影,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。
17、他和我上了车,把所有的橘子都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然后拍拍衣服上的泥土,心里很放松。
18、然后我看到了他的背影,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。我赶紧擦干眼泪,怕他看见,也怕别人看见。
19、我在这里读到,在晶莹的泪光中,看到那肥胖的,蓝色的布棉袍,黑色的布马褂的背影。
20、当我洗手的时候,日子是从水槽里流出来的;吃饭的时候,这一天是从饭碗里出来的;她一声不吭,就从她那呆滞的眼睛里钻了出来。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七
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,用得好时,又是一种艺术。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,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。我说满没有错儿;但是若统计起来,口的最多的(也许不是最大的)用处,还应该是说话,我相信。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,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“宣传”,自我的宣传。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。
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,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;我却也愿意让步,请许我这样说: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地为自己,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!自己以外有别人,所以要说话;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,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。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。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《祝福》,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。
一般人见生人时,大抵会沉默的,但也有不少例外。常在火车轮船里,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地到处向人问讯,攀谈,无论那是搭客或茶房,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;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,竟会不感觉一点儿疲倦!见生人的沉默,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,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。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,你全然不熟悉,你所能做的工作,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——像防御一个敌人。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。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,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——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?——;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,若他是个爱说的人。
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。假如这个生人,你愿意和他做朋友,你也还是得沉默。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,选出几处,加以简短的,相当的赞词;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。这就是知己的开场,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。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“大人物”,你记住,更不可不沉默!大人物的言语,乃至脸色眼光,都有异样的地方;你最好远远地坐着,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。——自然,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。若你愿意专诚拜谒,你得另想办法;在我,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。——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,准可以满足,而不用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。
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,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,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。至于自我宣传,诚哉重要——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?——,但对于生人,这是白费的;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,只暗笑你的宣传热;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,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。朋友和生人不同,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——宣传。这不用说是交换的,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。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,谅解你;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。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,他们就趣味地听着;你的话严重或悲哀,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,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。
在后一种情形里,满足的是你;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。他们知道“应该”怎样做;这其实是一种牺牲,“应该”也“值得”感谢的。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,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;同样的故事,情感,和警句,隽语,也不宜重复的说。《祝福》就是一个好榜样。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,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——你自己的心,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。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。
只有不可知,不可得的,才有人去追求;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,你对于别人,对于世界,将没有丝毫意义,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。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,你将不能支持自己,而倾仆到无底的黑暗里去。一个情人常喜欢说:“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!”谁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么呢?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,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,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;以后跟着说的,更只是“口头禅”而已。所以朋友间,甚至恋人间,沉默还是不可少的。
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,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——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?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。譬如在下午,在黄昏,在深夜,在大而静的屋子里,短时的沉默,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。有人称这种境界为“无言之美”,你瞧,多漂亮的名字!——至于所谓“拈花微笑”,那更了不起了!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。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,一主一客时,就不准行。你的过分沉默,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,赶跑了!倘使你愿意赶他,当然很好;倘使你不愿意呢,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,抽烟,看画片,读报,听话匣子,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,时局——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,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——,总以引他说话为度。于是你点点头,哼哼鼻子,时而叹叹气,听着。他说完了,你再给起个头,照样的听着。
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,他是一位准大人物,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。他坐下时,将两手笼起,搁在桌上。说了几句话,就止住了,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窘极,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。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,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。
(原载1932年11月7日《清华周刊》第38卷第6期)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八
回到北平来,回到原来服务的学校里,好些老工友见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话道:“您回来啦!”是的,回来啦。去年刚一胜利,不用说是想回来的。可是这一年来的情形使我回来的心淡了,想象中的北平,物价像潮水一般涨,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。然而我终于回来了。飞机过北平城上时,那棋盘似的房屋,那点缀看的绿树,那紫禁城,那一片黄琉璃瓦,在晚秋的夕阳里,真美。在飞机上看北平市,我还是第一次。这一看使我联带的想起北平的多少老好处,我忘怀一切,重新爱起北平来了。
在西南接到北平朋友的信,说生活虽艰难,还不至如传说之甚,说北平的街上还跟从前差不多的样子。是的,北平就是粮食贵得凶,别的还差不离儿。因为只有粮食贵得凶,所以从上海来的人,简直松了一大口气,只说“便宜呀!便宜呀!”我们从重庆来的,却没有这样胃口。再说虽然只有粮食贵得凶,然而粮食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。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,罩着北平的将来。但是现在谁都有点儿且顾眼前,将来,管得它呢!粮食以外,日常生活的必需品,大致看来不算少;不是必需而带点儿古色古香的那就更多。旧家具,小玩意儿,在小市里,地摊上,有得挑选的,价钱合式,有时候并且很贱。这是北平老味道,就是不大有耐心去逛小市和地摊的我,也深深在领略着。从这方面看,北平算得是“有”的都市,西南几个大城比起来真寒尘相了。再去故宫一看,吓,可了不得!虽然曾游过多少次,可是从西南回来这是第一次。东西真多,小市和地摊儿自然不在话下。逛故宫简直使人不想买东西,买来买去,买多买少,算得什么玩意儿!北平真“有”,真“有”它的!
北平不但在这方面和从前一样“有”,并且在整个生活上也差不多和从前一样闲。本来有电车,又加上了公共汽车,然而大家还是悠悠儿的。电车有时来得很慢,要等得很久。从前似乎不至如此,也许是线路加多,车辆并没有比例的加多吧?公共汽车也是来得慢,也要等得久。好在大家有的是闲工夫,慢点儿无妨,多等点时候也无妨。可是刚从重庆来的却有些不耐烦。别瞧现在重庆的公共汽车不漂亮,可是快,上车,卖票,下车都快。也许是无事忙,可是快是真的。就是在排班等着罢,眼看着一辆辆来车片刻间上满了客开了走,也觉痛快,比望眼欲穿的看不到来车的影子总好受些。重庆的公共汽车有时也挤,可是从来没有像我那回坐宣武门到前门的公共汽车那样,一面挤得不堪,一面卖票人还在中途站从容的给争着上车的客人排难解纷。这真闲得可以。
现在北平几家大型报都有几种副刊,中型报也有在拉人办副刊的。副刊的水准很高,学术气非常重。各报又都特别注重学校消息,往往专辟一栏登载。前一种现象别处似乎没有,后一种现象别处虽然有,却不像这儿的认真——几乎有闻必录。北平早就被称为“大学城”和“文化城”,这原是旧调重弹,不过似乎弹得更响了。学校消息多,也许还可以认为有点生意经;也许北平学生多,这么着报可以多销些?副刊多却决不是生意经,因为有些副刊的有些论文似乎只有一些大学教授和研究院学生能懂。这种论文原应该出现在专门杂志上,但目前出不起专门杂志,只好暂时委屈在日报的余幅上:这在编副刊的人是有理由的。在报馆方面,反正可以登载的材料不多,北平的广告又未必太多,多来它几个副刊,一面配合着这古城里看重读书人的传统,一面也可以镇静镇静这多少有点儿晃荡的北平市,自然也不错。学校消息多,似乎也有点儿配合着看重读书人的传统的意思。研究学术本来要悠闲,这古城里向来看重的读书人正是那悠闲的读书人。我也爱北平的学术空气。自己也只是一个悠困的读书人,并且最近也主编了一个带学术性的副刊,不过还是觉得这么多的这么学术的副刊确是北平特有的闲味儿。
然而北平究竟有些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说它“有”罢,它“有”贵重的古董玩器,据说现在主顾太少了。从前买古董玩器送礼,可以巴结个一官半职的。现在据说懂得爱古董玩器的就太少了。礼还是得送,可是上了句古话,什么人爱钞,什么人都爱钞了。这一来倒是简单明了,不过不是老味道了。古董玩器的冷落还不足奇,更使我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的地方,也萧条起来了。我刚回来的时候,天气还不冷,有一天带着孩子们去逛北海。大礼拜的,漪澜堂的茶座上却只寥寥的几个人。听隔家茶座的伙计在向一位客人说没有点心卖,他说因为客人少,不敢预备。这些原是中等经济的人物常到的地方;他们少来,大概是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了吧。
中等经济的人家确乎是紧起来了。一位老住北平的朋友的太太,原来是大家小姐,不会做家里粗事,只会做做诗,画画画。这回见了面,瞧着她可真忙。她告诉我,佣人减少了,许多事只得自己干;她笑着说现在操练出来了。她帮忙我捆书,既麻利,也还结实;想不到她真操练出来了。这固然也是好事,可是北平到底不和从前一样了。穷得没办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。我太太有一晚九点来钟带着两个孩子走进宣武门里一个小胡同,刚进口不远,就听见一声:“站住!”向前一看,十步外站着一个人,正在从黑色的上装里掏什么,说时迟,那时快,顺着灯光一瞥,掏出来的乃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!我太太大声怪叫,赶紧转身向胡同口跑,孩子们也跟着怪叫,跟着跑。绊了石头,母子三个都摔倒;起来回头一看,那人也转了身向胡同里跑。这个人穿得似乎还不寒尘,白白的脸,年轻轻的。想来是刚走这个道儿,要不然,他该在胡同中间等着,等来人近身再喊“站住!”这也许真是到了无可奈何才来走险的。近来报上常见路劫的记载,想来这种新手该不少罢。从前自然也有路劫,可没有听说这么多。北平是不一样了。
电车和公共汽车虽然不算快,三轮车却的确比洋车快得多。这两种车子的竞争是机械和人力的竞争,洋车显然落后。洋车夫只好更贱卖自己的劳力。有一回雇三轮儿,出价四百元,三轮儿定要五百元。一个洋车夫赶上来说,“我去,我去。”上了车他向我说要不是三轮儿,这么远这个价他是不干的。还有在雇三轮儿的时候常有洋车夫赶上来,若是不理他,他会说,“不是一样吗?”可是,就不一样!三轮车以外,自行车也大大的增加了。骑自行车可以省下一大笔交通费。出钱的人少,出力的人就多了。省下的交通费可以帮补帮补肚子,虽然是小补,到底是小补啊。可是现在北平街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,骑车不但得出力,有时候还得拚命。按说北平的街道够宽的,可是近来常出事儿。我刚回来的一礼拜,就死伤了五六个人。其中王振华律师就是在自行车上被撞死的。这种交通的混乱情形,美国军车自然该负最大的责任。但是据报载,交通警察也很怕咱们自己的军车。警察却不怕自行车,更不怕洋车和三轮儿。他们对洋车和三轮儿倒是一视同仁,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。曾在宣武门里一个胡同口看见一辆三轮儿横在口儿上和人讲价,一个警察走来,不问三七二十一,抓住三轮车夫一顿拳打脚踢。拳打脚踢倒从来如此,他却骂得怪,他骂道,“×你有民主思想的妈妈!”那车夫挨着拳脚不说话,也是从来如此。可是他也怪,到底是三轮车夫罢,在警察去后,却向着背影责问道,“你有权利打人吗?”这儿看出了时代的影子,北平是有点儿晃荡了。
朱自清美文摘抄篇九
1) 洗手的时分,日子从水盆里过来;吃饭的时分,日子从饭碗里过来;默默时,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来。
2) 路上只我一个人,背着手踱着。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;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,到了另一个世界里。我爱热闹,也爱冷静;爱群居,也爱独处。像今晚上,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便觉是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,一定要说的话,现在都可不理。这是独处的妙处;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。
3) 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,都很阔大,俨然是三座门儿;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,在桥下过去时,真是太无颜色了。
4) 天是蓝得可爱,仿佛一汪水似的;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。
5) 我们明知那些歌声,只是些因袭的言词,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;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,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,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,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。
6) 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: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,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。
7) 等到灯火明时,阴阴的变为沉沉了:黯淡的水光,像梦一般;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,就是梦的眼睛了。
8) 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,光光的立着;在月光里照起来。
9) 桥砖是深褐色,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;但都完好无缺,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。
10) 我们坐在舱前,因了那隆起的顶棚,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;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,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,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,便像是下界一般,迢迢的远了,又像在雾里看花,尽朦朦胧胧的。
11) 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,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,交互的缠着,挽着;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。
12)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,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,象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层层的叶子中间,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,有袅娜地开着的,有羞涩地打着朵的;正如一粒粒的明珠,又如天里的星星。微风过处,送来缕缕清香,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,象闪电般,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。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,这便宛然有一了道凝碧的波痕。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,遮住了,不能见一些颜色;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。
13) 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,不应该是一种,一国,一乡,一家的。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"洋鬼子".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,竟已被揿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。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,伸着脸袭击我了。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,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。他之来上海,或无多日,或已长久,耳濡目染,他的父亲,亲长,先生,父执,乃至同国,同种,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;而他的读物也推波助澜,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,以长他自己的威风。
14) 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,中间应该有街路?这些房子都破旧了,多年烟熏的迹,遮没了当年的美丽。
15) 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,交融着,使月成了缠绵的月,灯射着渺渺的灵辉;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,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。
16) 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,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。
17)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,地上的孩子也多了。城里乡下,家家户户,老老小小,也赶趟似的,一个个都出来了。舒活舒活筋骨,抖擞抖擞精神,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。"一年之计在于春",刚起头儿,有的是功夫,有的是希望。
18) 到徐州见着父亲,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,又想起祖母,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,"事已如此,不必难过,好在天无绝人之路!"20、层层的叶子中间,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,有袅娜地开着旳,有羞涩地打着朵儿旳;正如一粒粒的明珠,又如碧天里的星星,又如刚出浴的美人。微风过处,送来缕缕清香,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
19) 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,望见东关头了。
20) 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;灯光是浑的,月色是清的,在浑沌的灯光里,渗入了一派清辉,却真是奇迹!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。
21)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;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
23) 桃树,杏树,梨树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都开满了花赶趟儿。红的像火,粉的像霞,白的像雪。花里带着甜味;闭了眼,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,杏儿,梨儿。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,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。野花遍地是:杂样儿,有名字的,没名字的,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,还眨呀眨的。
24) "吹面不寒杨柳风",不错的,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,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,混着青草味儿,还有各种花的香,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。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,高兴起来了,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歌喉,唱出婉转的曲子,跟清风流水应和着。牛背上牧童的短笛,这时候也成天嘹亮的响着。
25)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,穿着黑布大马褂,深青布棉袍,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探身下去,尚不大难。
27) 荷塘的四面,远远近近,高高低低都是树,而杨柳最多。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;只在小路一旁,漏着几段空隙,象是特为月光留下的。树色一例是阴阴的,乍看象一团烟雾;但杨柳的丰姿,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。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,只有些大意罢了。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,没精打采的,是渴睡人的眼。这时候最热闹的,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;但热闹是他们的!我什么也没有。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。采莲是江南的旧俗,似乎很早就有,而六朝时为盛;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。
28) 那电灯下的人物,只觉像蚂蚁一般,更不去萦念。这是最后的梦;可惜是最短的梦!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,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,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。我们的梦醒了,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;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'情思。
29) 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;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。
30) 作者把自己八千多日子的流逝作了高度的概括,使时间匆匆而去的抽象化为"如轻烟""如薄雾",比喻共同,联想新奇。轻烟、薄雾瞬息被"吹散了",被"蒸融了",日子就是如此稍纵即逝。
31) 一眼望去,疏疏的林,淡淡的月,衬着蓝蔚的天,颇像荒江野渡光景;那边呢,郁丛丛的,阴森森的,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: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。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,纵横着的画舫,悠扬着的笛韵,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,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。
33) 他的从容,他的沉默,他的独断独行,他的一去不回头,都是力的表现,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。决不婆婆妈妈的,决不粘粘搭搭的,一针见血,一刀两断,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。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。无论如何,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,看看自己的孩子!谁也是上帝之骄子;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,是没有种的!
34) 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,淡淡的影子,在水里摇曳着。
35) 沿着荷塘,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。这是一条幽僻的路;白天也少人走,夜晚更加寂寞。荷塘四面,长着许多树,蓊蓊郁郁的。路的一旁,是些杨柳,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。没有月光的晚上,这路上阴森森的,有些怕人。今晚却很好,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。
36) 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,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,没有声响,也没有影子。
37) 几天心里颇不宁静。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,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,在这满月的光里,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。月亮渐渐地升高了,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,已经听不见了;妻在屋里拍着闰儿,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。我悄悄地披了大衫,带上门出去。
38) 远处--快到天际线了,才有一两片白云,亮得现出异彩,像美丽的贝壳一般。
39)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;看起来厚而不腻,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?我们初上船的时候,天色还未断黑,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,委婉,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,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。
40) 从东关头转湾,不久就到大中桥。
【本文地址:http://www.xuefen.com.cn/zuowen/3467008.html】